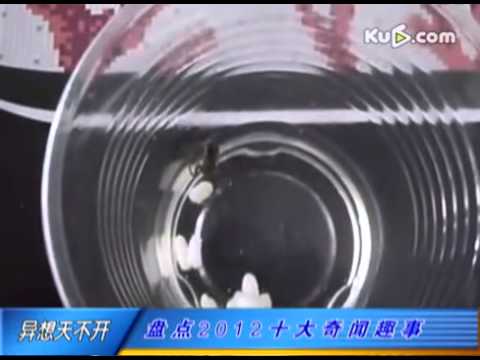【鉴于自焚藏人已逾百人,现将袁红冰先生所著《通向苍穹之巅——翻越喜马拉雅》在网络刊载,以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声援与敬意。 ——《自由圣火》编辑组】
看中国配图(图片来源:《西藏旅游》)
第十一章 哲人把背影留给美人(下)
——他的红焰之心却被青铜色的风吹散
苍白的雪的色泽覆蓋了他的视野,可金圣悲却觉得眼前只有永恒的黑暗。他相信,只有让自己的血如花雨飘洒在白雪上,丰饶的虚无才能够呈现出来——圣洁而丰饶的虚无,那时-空之巅的绝对真理,需要美男子的灼热之血的献祭。凝视著这个信念,金圣悲的眼睛里涌现出心迷神驰的向往,他看到关于一个哲理的形象的表述:一位以太阳为心的男子,在意义的引导下,走到命运的尽头;他用银柄的利刃的亲吻,刺碎炽烈的心,让血喷涌而出,迸溅在洁白如初雪的虚无上。
“噢,在洁白的虚无上盛开的男儿之血,是生命艺术之花,是人格之美殷红的极致;唯有血染的虚无,才配以绝对真理的名义成为英雄男儿的终极安慰!”金圣悲向那哲理的象征发出礼赞,而他的思想纯化为一个渴望:
“以形而上的生命唯美主义为基础,如果我创立的英雄人格哲学升华为信仰——当然是属于壮丽的男子和灿烂的美人的信仰,那麽,就让血迸溅在虚无上,成为生命艺术的最高形式和心灵意义的最后表述吧。绚丽璀璨的血染的虚无,乃是在生与死的锋刃上起舞的真理。”
金圣悲曾经被日本武士道进入死亡的方式震撼。那种由晶蓝的刀锋、雪白的长绸和女人残花般的吻痕陪伴的死亡方式,呈现出悲怆的雄性之美。但是,武士道的死亡方式由于缺乏对虚无意境和终极真理的理解,而显得单薄,不能最终感动金圣悲的哲人之心;切腹过程中,即使英雄意志也难于抑制的肉体的痛苦抽搐,又使这种死亡方式露出几许物性的阴影,缺少信念的完美感,因此无法魅惑金圣悲那颗唯美的诗者之心。更重要之处在于,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武士道不仅没有展现出拯救天下苍生的大悲情怀,反而被用来侵略他国,屠戮弱者,从而千古蒙羞。此刻,金圣悲的思想越过武士道死亡方式的千古遗恨,走进更加令人迷恋的死亡之美。
“找到高贵的死亡方式,是生命意义化的前提;使死成为信仰的实现,成为哲理的庆典,生命进程才能美如史诗。既然如此,就让我的血染红洁白的虚无吧… … 。”金圣悲的心沐浴在大海般动荡的喜悦中。就在试图俯身从靴筒中抽出蒙古短刀的瞬间,他却突然发现,自己的肢体仿佛枯死百年的朽树一样麻木,被冻裂的生命感觉已经极其遥远,而距离虚无的意境似乎更加遥远。
金圣悲僵直的身体重重摔倒在荒凉的白雪之上,犹如被命运之风吹倒的墓碑。命运对他太冷酷,冷酷得甚至剥夺了他以美丽高贵的死亡方式回归虚无的权利。这时,他听到了那位藏族少女的呼唤。那呼唤声像是来自时间之外,又像是来自他的生命深处。然而,金圣悲却竭力让自己的意识迅速地消失在苍白的黑暗中。对于高傲的男人,只能被女人拯救,是一种难以清醒面对的耻辱。
就芸芸众生而言,时间是生命的终极尺度,而拥有主体自信的心灵,则是时间的尺度——时间在意识中存在;意识丧失,时间便由于失去主体的确认隐入黑暗的未知意境。
金圣悲在时间之外停留了一天一夜,才又被微弱的意识之风吹回到时间中。意识到的第一缕芬芳就使他的心灵迷醉了。芳芬中有牡丹花的富丽,却又比花香更接近艳美的情欲;芳芬间飘拂着白杨林的清新,却也比林香更浓郁。那气息似乎是淡金色的,香得格外灿烂,仿佛苍穹高处被太阳点燃的白雪的氲氤,却又比燃烧的白雪更温柔。
“呵——,定然是她在用体温融化我冻僵的身体… … 。”这个思想如晶莹的刀锋,在金圣悲的意识间刻出一个微笑。虽然身体的感觉仍旧像朽木一样麻木,不过他还是领略到年轻女性身体柔美的风情与神韵。这或许是因为,那种柔美的魅力可以赐给朽木绿意盎然的生机。
金圣悲睁开眼睛,微弱的光从盖在身体上的毛毯旁边的缝隙间透进来,他逼近地看到一片顽石都会由于激动而为之破碎的炫目的白色。金圣悲明白了:自己的头颅是躺在少女的胸怀间;芳香的乳房正以丰盈的轮廓隆起在他紧闭的双唇旁;乳房之巅,浅红色的乳头还没有充分发育,娇艶得像一小片朝霞。
金圣悲没有想到,面容被高原的太阳晒成青铜色的少女,身体竟然白得如此迷人魂魄。他化为死灰的心被一个美艳的冲动点燃了——他想用炽烈的狂风与猛兽之吻,在少女洁白的身体上,烧灼出殷红的吻痕。但是,他却没有那样作。这并非因为他的双唇仍然冰冷如霜,而是一种陌生的感觉阻止了他:似乎他的灵魂同少女妖娆的身体之间,隔着比时间还漫长的宿命的废墟。
为击碎这种感觉,金圣悲缓缓抬起目光,寻找少女的眼睛。没有任何理由,金圣悲就相信他的心灵同少女的灵魂并不陌生,而在形而下的现象世界中,少女的眼睛正是她灵魂的栖息之地。
金圣悲首先看到,少女的面容因羞涩的红晕而美丽绝伦。片刻之后,当他们的目光相遇的瞬间,两人都同时会心地一笑——金圣悲的笑意辉煌如天边深红的落日;少女的笑容璀璨似萦绕于落日间的流霞——一笑之际,瞬间便已超越永恒:在时间之前,他们就难解难分地构成同一个审美的意境,就是同一缕审美激情的双翼,就是同一滴从审美激情的伤痕间垂落在苍穹之巅的血。
如痴如醉的对视间,一尊双身佛像从金圣悲苍茫的心灵中涌起,呈现在太阳之巅:神态狞厉的大威德金刚,将身形纤秀的少女搂在胸前,以极端的体态,作彿学哲理之舞;大威德金刚与少女忘情的对视,构成那彿学哲理的舞姿之魂。金圣悲不禁想到:“他们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?”
双身佛像倏然之间便被太阳焚化为金色的虚寂,金圣悲则从与他对视的少女那晶莹得近乎灿烂的眼睛里,看到了,或者更准确地讲,是用心领悟到无我的意境。而此刻思想又成为他生命的主题。
“把心给了我,少女就进入无我的意境——情爱的追求,引领她进入高贵的哲学。可是,我,一个坚逾铁石的意志,一个锐利如刀的个性,一个渴望挥动雷电、踏着时间起舞的诗者,难道也会丧失自我吗?是的,‘我’正在消融,正在湮灭于少女眼睛深处的无我的意境… … 。”
“‘我’湮灭了,心灵虚化为浩荡的感动。从‘无我’的意境中涌现出的,是芬芳的虚无。芬芳来自少女的妖娆,虚无则是‘我’的皈依。连‘我’都只表述虚无,那麽,附着在‘我’之上的本能欲望和尘世的欲望,又怎能真实。噢,对于心灵,真实的,唯有虚无。”
“可是,在虚无中涌动的浩荡的感动又意味着什么?芸芸众生终生都承受欲望之火焚烧的苦痛,或许,那属于虚无意境的感动,就是恤悯天下苍生的佛的大悲之情。引导人类理解万欲皆虚,唯虚无为真的绝对精神,是引领人类走出苦痛的真理之路。噢,大悲之情——我已经进入佛境。”
“原来,少女红杏花般妖娆、春雪般洁白的身体,才是通向虚无的美和智慧之门。让自我消逝于少女无我的情爱,让心灵领悟虚无的感动,乃是比生命的死亡更深刻的湮灭——少女华彩熠熠的身体和情爱,是浮雕于虚无之上的智慧的花枝… … 。”
金圣悲意识到,他此刻关于佛的意境的灵感来自于那尊双身佛的启示。不过,尽管都使情欲升华为哲理,密宗与金圣悲之间却有一个区别:密宗是以身体的修炼实现情欲的升华,金圣悲则是借诸审美激情,将形而下的情欲之美,熔铸成虚无之镜。
在虚无的意境中,金圣悲由于消融为一缕无我的大悲之情,而超越永恒与无限。渐渐地,随着冻僵的身体在少女的依偎间恢复知觉,金圣悲也由哲学意境重返人间。而最初的感觉便是烈焰焚身般的疼痛。然而比属于烈焰的疼痛更绚丽的感觉却来自少女的身体——温柔、芳香,风情万种而又纯洁如雪。
一个静谧的清晨,金圣悲发现焚身的烈焰熄灭了,少女的搂抱也伴随着疼痛一起离去。从那一天起,少女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到外面去看护羊群,夜里则一个人睡在帐房的另一边。少女不再同金圣悲交谈,甚至不用目光交谈,即使为金圣悲冻伤的手指换敷藏药时,少女也从不与他对视。少女沉默得真像一位青铜铸成的美人。
诗者对美人的心意最敏感。金圣悲知道,少女在等待一个命运的召唤,等待得心都要干枯了。可是,他却不能发出召唤,让少女变成一朵在他心间盛开的花。少女美丽迷人的身体已经成为金圣悲心灵的圣物;从少女芳香的搂抱为他开启通向佛境之门的那一刻起,他们之间的情缘便断绝了。因为,任何飘摇著情欲的亲吻和爱抚——即便亲吻中有太阳的神韵,爱抚间起伏著雪水河波浪般的柔情,也会亵渎了少女圣洁的美。
在心灵的回顾中,金圣悲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,那天他能在少女香艳的搂抱中毫不动情,湮灭于无我的大悲之境,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身体和情欲冻结在失去感觉的僵硬状态,而不是因为他有一颗铁铸的彿心。否则,他同少女只能书写一个属于荒野的爱情的诗篇,而不能升华为达到形而上极致的哲理——同岩石在一起,他是沉迷于思想而欲望凋残的哲人;同美人在一起,他是情欲辉煌的诗者。现在,雄性的情欲正在复活,他听到了自己生命深处回荡的野性如狂的呼啸。于是,金圣悲准备身体一旦恢复到能够远行的程度,便立刻离去,只为了不亵渎少女莹白的身体,他心灵的圣物。
少女变得更加沉默了,沉默得像一块顽石,她似乎预感到金圣悲即将离去。只在深夜,金圣悲才会听到从帐房另一边的暗影中传来压抑的抽泣声。那是沉默的顽石在哭泣——从深夜直到黎明。只有他离去前的最后一个夜晚,帐房里飘起少女哀伤的歌声。金圣悲则默默地喝完随身携带的最后一瓶烈酒。他看到少女眼睛里涙影如繁星;只不过他自己也不知道,他是用眼睛,还是用心看到的。
离去的时刻就像死亡的宿命一样来临。分别时,没有泪水,没有祝福,只有两双互相凝视的“无我”的眼睛,他们都把心给了对方。金圣悲离去了,他从少女的肉体上摘取一缕金色的芳香,挂在自己生命的枝头。少女走上岩石破碎的山岗,用遥望为金圣悲送行。朝霞将山岗开裂的岩石映成艳红,宛似雷电雕刻出的红莲花,少女则像端坐莲花间的菩萨。当地平线遮住少女的身体那一刻,浩荡的风中隐隐飘来一个哀伤的声音:“记住,我叫梅朵… … 。”
离开圣洁而荒凉的西藏高原,回到低地,回到挤满心灵腐烂于物欲的人群中,金圣悲却感到世界更加荒凉。他本想以大悲之情,从事拯救人的灵魂的事业,却又发现自己的心丢失了——丢失在梅朵的眼睛里。无心即无我,按照彿理,他应当因为无心而得到宁静的喜悦,但是,他却陷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中。由此,金圣悲理解了他的生命哲学与彿学哲理的不同。
“彿学哲理以大悲之情为精神价值的极致,我的心灵却不能止步于大悲。我要追寻大悲之后,虚无之中的审美激情。大悲是拯救苍生的高贵愿望,虚无的真理则是拯救苍生的终极安慰。然而,如果失去了对审美激情的理解,虚无的意境就太荒凉,终极安慰就太缺乏情感的丰饶。唯有怀抱对美的信仰,回归虚无,人类才能使生命的意义与虚无一致。”
“是的,为追寻审美激情,我必须找回我失落在梅朵眼睛里的心。因为,美是只在峻峭的个性之巅筑巢的鹰;没有个性就没有美,而失去了心,也就失去了个性。噢,在湮灭于虚无的宿命前,依然为美而坚守峻峭的个性——这难道不是最具英雄情怀的哲理吗。”就怀着这样的信念,金圣悲曾经又一次走上西藏高原,去寻找失落的心。
那一天,当金圣悲看到身披僧衣的梅朵被雷电击中而燃烧起来的刹那间,遗憾就已刻在他的白骨之上:“如果刚才我再靠近一些,现在就来得及奔跑过去,搂住梅朵,踏着狂风的舞步,进入燃烧的虚无——燃烧的虚无,那或许是哲理所能达到的极致之美了。”
命运没有给金圣悲机会,同梅朵美丽的肉体一起湮灭于燃烧的虚无;梅朵却还给他一颗风中的火焰之心,以及永远不会消失的烈焰焚心的痛苦——直到他寻找到藏人之魂。为流亡者遗失在翻越喜马拉雅之路上的白骨和红血,寻找灵魂的归宿,可能正是梅朵的愿望。
金圣悲本以为只有找到藏人魂,红焰之心才会熄灭,灿烂的疼痛才会消失。现状,虽然苦苦地追寻,他依然不能确定该如何去表述藏人之魂的意境。可是,他的心焰却在回顾时,由于紫衣少女变得荒凉的眼睛而意外地突然熄灭。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,只是燃烧的心熄灭之后,生命一片黑暗——生命笼罩在黑暗中,外部世界即使阳光明亮,人也看不清该走向何方。
那一天,金圣悲坐在一辆越野车中,驰下达兰萨拉的群山。旁边的印度司机沉默得像一片散发出浓郁汗味儿的阴影。而金圣悲则万念俱灰,只凝视著狰狞的黑暗,怀念烈焰焚心时曾经的金色的疼痛。
(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)来源:《通向苍穹之巅》
短网址: 版权所有,任何形式转载需本站授权许可。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.
【诚征荣誉会员】溪流能够汇成大海,小善可以成就大爱。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: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,成为《看中国》网站的荣誉会员,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,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,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,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。